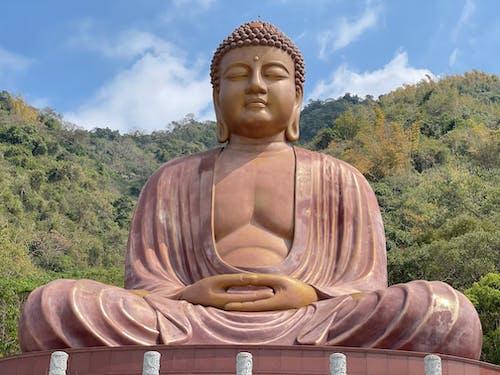阿难问佛陀:为何说“十八界”,也是以如来藏真如自性为本体?上

阿难问佛陀:“为何说十八界,也是以如来藏真如自性为本体呢?”
佛陀说:“眼根与色尘相结合,就生出眼识。此识是依眼根所生,以眼为识的界限而称之为界呢?还是依色尘所生,以色为识的界限而称之为界呢?”
如果是依眼根而生,就没有作为识的对象的色相和虚空,没把此二者分开,即使有识,也是没有用处的。所见的不是青、黄、赤之色,又无长、短、方等性状可以表现,眼识从何处设立界限呢?
如果说眼根依凭色尘而生,观无色之虚空时,色尘已经消失,眼识就应当消灭。识既然已经消失,就没有了能觉知色相的主体,为什么观看虚空时,眼识又能辨别虚空性呢?
色尘变迁时,如果眼根不随之变迁,又从何建立眼识界呢?
但若说眼根随色相变迁而变迁,二者都在变动,界限也无从建立。若说眼根不随色相变迁而变迁,眼识就成了永恒的存在,既言此识依色尘而生,当然就不能识知虚空的所在。
如果说眼识是兼根、境二者共同生成,那么,它是眼根、色相相结合而生呢?还是相分离而生呢?
如果是二者相和合而生,和合之中仍有缝隙;如果是二者保持一定距离而生,眼识就被分成两半,一半有感觉,一半无感觉,体性杂乱,怎能成立一眼界呢?
因此,应当知道,眼根、色尘为缘生眼识的说法,向三处推究都无所得。也就是说,眼根、色境及眼识三界,都是依如来藏自体而起的虚妄暂有的现象。既不属于因缘所生,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。

佛陀告诉阿难:“耳根和声尘相互为缘生出耳识,耳识是因耳所生,以耳为界?还是由声所生,以声为界?”
如果是因耳根而生,以耳根为界,则声尘须具有运动和静止两种状态,才能形成耳识。动、静两种相状若不现前,单靠耳根是不能有听觉的。听觉既不存在,耳识又是什么形貌呢?
若耳识从耳闻而来,没有动、静两种声尘之时,能闻之根也无从建立,怎么能生识呢?
若说肉耳能生识,可肉耳属于身根的色相,身根的对象应该是触尘,因此怎么能把耳形之身根当作能闻,并因而称其为耳识界呢?耳识既非闻根肉耳所生,它又能从何处立界呢?
如果耳识是声尘所生,则不关耳闻之事。声必因尘而显现,若无闻听,也就没有声相之所在。声尘既已亡失,如何能生识呢?
再者,耳识依从声尘而生,也就意味着声音也是因闻而有。闻声之时,也就应该能听到耳识的相状。倘若并非如此,就不能称之为耳识界。
但是,如果能听到耳识的相状,此识就等同于声尘,即所闻。这样,作为能闻的主体又是谁呢?如果不存在能闻的主体,人岂不等同于草木了?
也不应该说声尘与耳根相混合构成中界,混合则应该没有分界。这样,在内根与外尘之间于何处建立界相呢?
因此,应当知道,耳根与声尘互相为缘生耳识的说法,从三处推究都无所得。也就是说,耳根、声境、耳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真如自体而起的虚妄作用。既不属于因缘所生,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。

佛陀告诉阿难:“鼻根与香尘互相为缘生出鼻识,鼻识是从鼻根所生,以鼻根为界?还是依于香尘,以香尘为界?”
如果它是从鼻根所生,则心中是以何为鼻的?以如双垂爪的肉形为鼻?还是以嗅知、呼吸的性能为鼻?
如果取脸上之肉形为鼻,肉质乃属身根,其认知对象当然是触尘,而绝不能是香尘。鼻根之名尚且得不到,为何能说此识是鼻根所生并以之立界呢?
如果取嗅觉为鼻识,则以何者为能知呢?如以鼻肉为能知,但肉之知觉本来属于身根,其触觉作用并不属于嗅觉功能。
如果以鼻孔内之虚空为能嗅知,则是此虚空自己具有知觉,鼻肉应该没有感觉。鼻肉既无知觉,全身也就应该没有知觉。以此而论,因为虚空是没有所在的,因此人也就会无处可以存在了。
如果认为鼻识是香尘所生,则此知觉当然属于香尘,与人就没有了关系。
香味、臭味如果都是从鼻孔产生,则它们就应该不会从伊兰树和旃檀木产生。此极臭和极香的两种气味不来的时候,人嗅自己的鼻,究竟应该是香,还是臭呢?
是臭就不应是香,是香就不应是臭。如果两种气味都能嗅到,一人就应该有两个鼻,究竟哪一个是真体呢?
如果说只有一个鼻却能同时闻香和臭,则香、臭已混和为一,没有区别了。香、臭既然都没有自性,则鼻识之界从何建立呢?如果鼻识因香尘而生,鼻识也因香尘而有嗅的功能。
但如同眼有见性却不能看见眼睛一样,鼻识虽有嗅的功能却同样不能自嗅其鼻。鼻识既然从香尘生,也应该不能自知其香才对。
如果鼻识能够知道香,就不能说是香生识;如果不知道,则不可叫作鼻识。
香若不靠嗅,则不知有香,香界就不能建立。鼻识若不知道香,所谓因香尘而建立香识界就无从谈起。
鼻根属内,香尘属外,并无处于其中间的鼻识,则内之鼻根、外之香尘都不存在。所谓的能嗅之识,当然也就是虚妄的了。
因此,应当知道,鼻、香为缘生鼻识界的说法,向三处推究都不能确立,所以,鼻根、香境、鼻识都是虚妄暂有的现象。
也就是说,鼻根、香境、鼻识三界都是依如来藏自体而起的功能、作用。既不属于因缘所生,也不是无因自生的自然之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