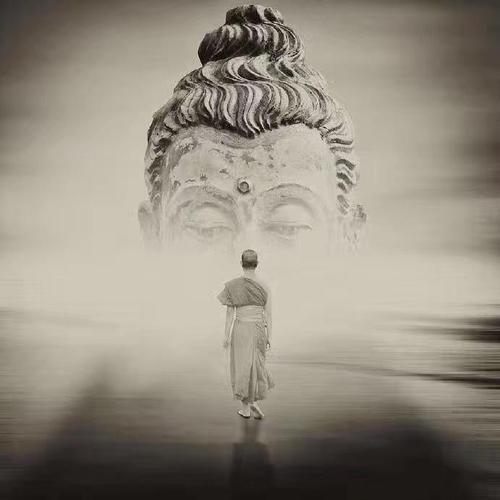高僧玄奘传:离开龟兹继续前行,不料却遇到了大批的强盗

玄奘离开龟兹继续前行,不料却遇到了大批的强盗。
一方是兵强马壮,虎势眈眈的悍匪,而另一方就是带着大笔盘缠、手无缚鸡之力的玄奘。强弱差距如此之大,玄奘又是如何逃脱险境的呢?
玄奘遇见的那批强盗是突厥强盗,总共有两千多人,而且还都骑着马,几乎相当于一支军队了。
要知道,玄奘刚刚带着高昌国王给他的一百两黄金、三万银钱,带着五百匹绫绢,又路过龟兹国,龟兹国王也不会少给他布施,因此,在这群强盗眼中,玄奘俨然成了大财东。
但这群强盗先不下手,因为他们觉得玄奘已经是瓮中之鳖,所以就先商量着怎么分玄奘的东西。
可能是由于商量不出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分赃办法,说着说着就自己打起来了,而且还越打越远,最后居然就把玄奘给留在那儿了,玄奘这才捡回一条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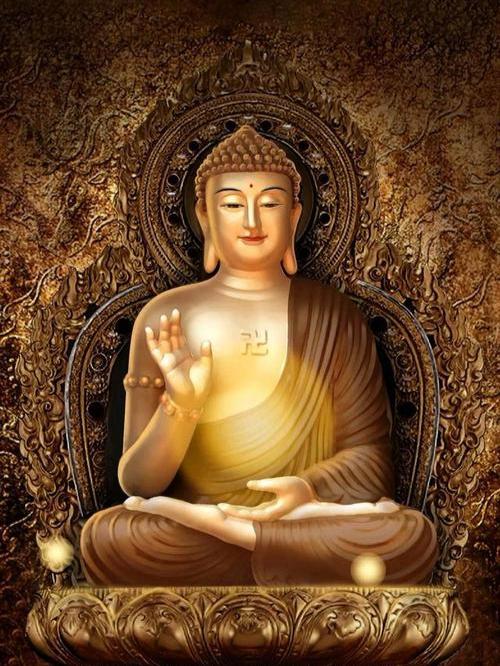
玄奘接着往西走了六百多里,穿过一个小沙漠,到了跋禄迦国,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,他在此地停留了一天,略事休息。
再往西三百里,又穿过一个小沙漠,就来到了凌山脚下,也就是葱岭的北麓。这是既是交通要道,却又非常艰险,凌山是著名的冰山,海拔七千多米,险峻异常,常年积雪,很难通行。
那里找不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可以停留,连垒一个灶都垒不起来,只能把锅子吊起来,底下点上柴火做饭,睡觉时也只能躺在冰上。
就这样,一共经过七天,玄奘一行人才走出了冰天雪地的凌山。
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损失也是惨重的,据记载,和玄奘一起来到凌山的人中“十有三四”没有能够熬过这一段路,当然这些人包括从高昌带过来的很多随从,可能还有一些和他一起结伴走的商人。
至于牲口的损失,那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了。

玄奘走出凌山之后,继续往西约行走了四百多里,就是大清池。
它另外有两个名字——热海、咸海。它叫“咸海”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它是个内陆湖,那里的水又苦又涩。
至于“热海”这个名字就有点意思了,因为那湖水的温度只不过是不结冰而已,绝对不是热气腾腾或者有温暖的感觉的。
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伊克塞湖,它在同治三年(1864年),由于中国和当时的俄国签订了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,才脱离中国的管辖。今天在俄罗斯境内,它也是个旅游胜地。
由于玄奘没有办法渡河,所以他只能绕着湖走,差不多向西走了五百多里之后,他到达了碎叶城。
这里一度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,公元679年,王方翼曾在此地筑过城池。可是,这都是在玄奘来过这里之后很久的事情了。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,这里应该还比较荒凉。
碎叶城的遗址今天已经被发现了,就在今天俄罗斯的托克玛克境内。

玄奘在碎叶城遇见了强盛的突厥王朝可汗,叶护可汗。
幸好高昌王早就给叶护可汗准备了厚礼,并且写了一封信,恳求叶护可汗帮助玄奘走出西域,但玄奘和突厥可汗的一番对话,竟酿成了一个千古误会。
我们知道,作为一个游牧民族,突厥可汗庭基本上是马背上的一个朝廷,他们不是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,而是经常会移动。游牧民族总是逐水草而居,随着水草的丰盛与否,随着气候的合适与否,不断搬动自己的行政管理中心。
当玄奘到达碎叶城的时候,恰好叶护可汗也在那里,因此两人就碰上了。
叶护可汗见到玄奘后非常高兴,他给了玄奘一种特殊的礼遇。叶护可汗派官员先把玄奘送往可汗衙安置好,自己接着打猎。三天后,可汗打猎回来,将玄奘请到可汗居住的大帐篷里。
这也不是一般的帐篷,而是“金华装之,烂眩人目”。
达官贵人在可汗前列成两排侍坐,后边还站着拿着武器的警卫武士。这样的排场,让已经很见过世面的玄奘也不由得心生赞叹:“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。”

停留了几天后,玄奘准备继续他西行求法的征途了。
可汗很是友善,在军队里寻找通晓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的少年,封他们为官,一路相送。照例还有丰盛的施舍,并且率领群臣送出十余里。
有趣的是,叶护可汗在玄奘决定动身时,劝玄奘说:
“师不须往印特伽国,彼地多暑,十月当此五月,观师容貌,至彼恐销融也。其人露黑,类无威仪,不足观也。”
这里首次出现了“印特伽”这个名字,就发音而言,似乎和“印度”很接近了。那么,“印特伽”后来怎么就变成“印度”了呢?
我们知道,在隋、唐以前,汉语中用来称呼南亚次大陆那个神秘国度的名词并不统一,相反,很是杂乱,最常见的就有“身毒”、“天竺”。
而当时中亚、西域流行的各种各样伊朗语,倒是比较一致,大体上都是hindu、indu,大概都是从indus(印度河)来的。今天西方语言的India、Indien都是从这里来的。但是也都是模糊的,不那么明确的。
玄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混乱矛盾的,因为印度的居民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名的,那些遥远地方的人,才模模糊糊地说个大致的总名而已,为了形容它的美,叫它“印度”。
这可就奇怪了,“印度”明明是玄奘才开始使用的啊,而且“印度”的意思居然还是“月亮”。